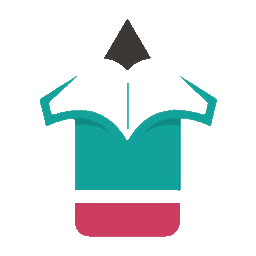第98章
关于徐稚柳之死,若说还有什么疑窦未解的话,可能要追溯到更早时候——
万庆十一年梁佩秋生辰当夜,文石溺死于护城河。张文思在接连多日莫名出现的纸团恐吓下变得疑神疑鬼,就连心腹王进都遭了他的怀疑。
此时,十多年前就该投河自尽的文石尸首离奇出现在衙门,张文思被吓破了胆,当场晕厥。此举引来多方怀疑,安十九作壁上观,顺着夏瑛的调查摸到了文定窑消失的数十万两雪花银。
这无疑是一桩牵扯巨大的舞弊案。
一时间魑魅魍魉齐聚一堂,亟待揭开背后神秘的面纱。与此同时,张文思敲响云水间的大门。
那是徐稚柳等待已久的一天。
也是那一天后,景德镇的形势急转直下,徐稚柳和夏瑛相继殉身,张文思开始求神问道,安十九一方独大。
而这一晚,当张文思在“清静无为”的修炼中缓缓转醒时,七真殿已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天黑了,应是晚间。
张文思推算时辰,料此刻或是酉时三刻。他这次打坐从午后开始,至此圆满完成一次道修,难得有了几分离境坐忘的意味,多日积攒的疲惫一扫而空,整个人如坠云端,飘飘欲仙。
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不对。
往常这时候护卫们虽不敢轻易入内打扰,至少会在门外点起火烛,以供照明。而今日四周非但没有半点光亮,观宇也好似安静过了头。
就在他起身预备唤人之际,殿内忽然蹿起一束火苗。
张文思循光看去,供奉着三清老祖神像的暖阁内,一道身影出现在层层垂落的帷幔后。
“张文思,你还记得我吗?”
这人声音沉而内敛,有些熟悉。张文思先问:“你是何人?怎的在此?”旋即打量周遭,微妙的直觉得到验证。
在这间为清修而建只留有一道窄门的屋内,四处挂满厚重的明黄色帷帘,严肃谨慎地配合着道家先祖的一举一动,然而此刻,微弱火烛下,除了一张张雕刻粗陋面无血色的道祖面孔明灭闪烁着,便只剩一抹超出寻常的、过分的静谧在悄然流动。
那静谧让张文思感受到了一种无限接近死亡的危机感。
他大喊道,“来人!一个个吃干饭的东西都跑哪去了?真当本官被降职就没法子整治你们了吗?玩忽职守不敬上官,看我这次回衙门……”
不待他说完,对方发出极轻的一声笑。
笑声轻蔑,伴着旷室里的回音,显出几分诡异。
“你笑什么?”
“张大人不会还看不明现状吧?若真有人想救你,岂会容我入内?”
“你休要挑拨!”
张文思想到王进,王进还是可信的,便大叫王进的名字,谁料回声响彻在殿宇,始终没有回应。而那人只是冷然看着他挣扎,不置一词。
张文思的心直直往下坠。
“你是谁?你究竟是谁?!”
“这么快就忘了我吗?看来那些纸团还没让你吃够教训。”
张文思一震,很快想到一人,再联想这人的身形,声音和感觉,无端端肖似那人。可那人已经死了,莫非鬼魂在作祟?
否则、否则怎敢?怎可能……
他瞬间汗毛倒竖,厉声喝道:“徐稚柳?你是徐稚柳?!不可能!他已烧成灰烬了!你别给我装神弄鬼,有本事出来说话!”
说完等不及穿好鞋履,他立刻朝着帷幔扑去,然而双手一抱,什么都没有。
声音却陡然在背后响起。
“张大人日理万机,忘了我不要紧,不会连文石也忘了吧?”
张文思反身朝着声音的来源又一个猛扑,再次落空。
“当年唆使文石作伪证陷害忠良,可有想过会有今日的报应?”
“报应?哪来的报应!”张文思怒吼着,再次奔向身影。他倒要看看今晚这一出七真殿闹鬼事件,究竟是冤魂不散,特地回来找他索命,还是谁在故弄玄虚!
“张大人醉心官场,多年钻营,若非心虚,怎舍得放弃那荣华富贵,躲到深山老林过这苦日子?”
“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躲到这里,你恐怕早就遭了黑手,步夏瑛后尘了吧?”
“安十九知道你隐匿于此吗?”
“你不会以为拿求神问道当幌子,就能躲一辈子吧?躲得再远,也仍在黄土之内,人间那帮恶鬼怎舍得放过你?”
“你可知万寿瓷钦银也和文定窑数十万两白银一样不翼而飞,安十九正在调查元凶,文石已死,你是仅剩的线索,总不能随便断了。”
细细密密的笑徘徊在七真殿的每个角落,伴随着鬼魅般投向墙面巨大的黑影,张文思浑如提线木偶一会扑向左一会奔向右,一会转前一会调后,连遭戏耍,气喘吁吁,慢慢地他的身体感到再次被掏空的疲惫,精神也回到萎靡的低谷。
这并非一日修行可以补足的元气,正如道法所言,他的内在已经空虚了,长达数月的担惊受怕和夜不能寐将他一再逼退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之所以还没崩溃,缺的大概就是今晚这根稻草。
“说吧,万庆十一年冬在云水间的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文思终于放弃了挣扎,在一种近乎于蛊惑的作用下,思绪滑向那一晚——那是他在接受文石“死而复生、而又复死”的现实后不久,联想先前出现在身边的纸团,他意识到在这背后有双无形的手,正在翻查文定窑一案。
他怀疑过身边许多人,最终将怀疑对象锁定为——徐稚柳。
他的怀疑并非没有依据,那阵子他在调查王进和钱庄的关系,将文定窑旧案翻了出来一再审视,于是当年不曾注意的细节、巧合,此时都变得微妙起来——文石不仅是文定窑的家主,还是另外一宗案子的人证,而那宗涉案的被告,名叫徐有容。
案卷上清晰记载了徐有容的生前,其本为江西出名的大才子,被数位老翰林认定为新翰林不二之选,因家境困窘而休学。
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重点是,其膝下有一子,名叫徐稚柳。
这种一字不差的名字,会有重名的可能吗?答案微乎其微。刹那间,过往种种闪过脑海,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在回到景德镇后,和徐稚柳的几番交手,那个少年人对他总怀着一种克制的敌意。
原来症结在此。
那时他任浮梁县县丞,县令是个三不管的闲人,大小事皆交由他料理。
平日托人找关系给他塞钱的数不胜数,他通常来者不拒,能帮则帮,上下一起吃黑,县令也睁只眼闭只眼,因此他在县内地位不可小觑。
一日,有人找到他主持公道。堂审后方知是宗奸淫妇女的案子,被告是当地乡绅们颇为看重的秀才老爷,他不敢妄断,仔细审理,奈何人证物证俱全。对方给的又多,明言想早点结案,以便原告女子入土为安。
这需求合情合理,他想想没什么大问题就给办了。案卷送上去没有多久,复核为秋斩,他依律行事,虽则人证文石的身份过于蹊跷,加之文定窑事发,数十万两银钱不翼而飞,他也存过疑虑,但正因涉案情形严重,而一向三不管的县令也提醒他莫管闲事,他便没有理会徐家人几次三番的上诉。
后来他被调去州府,又重回景德,来来去去一直在江西打转,原先以为是顶头上司不作为,故意压他,如今想想,兴许有人不想他出江西呢?
这也是他近日才参悟的道理。
去找徐稚柳那一晚还未深思到这一步,纯粹怕事发连累政绩一辈子出不了江西,上赶着去试探徐稚柳调查到了哪一步。
那一晚的情形他记得很清楚,徐稚柳似乎等待已久,并不需他怎么绕弯子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怀疑,表示文石受人唆使作了徐有容案子的伪证。又问作为主审的他,当时可有什么未指出的疑点。
他能说什么,断然道:“这两宗案子没有任何关联。我劝你也不要再查下去,若让人得知你父亲曾是奸淫女子的罪人,于湖田窑大有不利,于你自身也无好处。”
徐稚柳并不畏惧“罪人之子”的名头,便如一根利箭搭在弦上,绷紧已久,到了不得不发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婉娘之死是徐稚柳的手笔,便也不知徐稚柳曾经放过他一次,绝无可能再放过他第二次。对徐稚柳而言,这个时机更是千载难逢的,他已在收集安十九的罪证,亟待与夏瑛联手写下最后一笔。若能一次取得父亲含冤而死的证据,当然再好不过!
这是徐稚柳最后一片青天。
他曾失守太多次,已无能力再失去。他抱着必死的决心等待那一刻。
“或许只有事情闹大了,我才能借势为父亲洗刷冤屈吧?否则以我一己之力,如何与这滔天的权势相斗?”
“你……你既知晓,就该收手。徐稚柳,肉体凡胎只一条命,没了就什么希望都没了。”
“是吗?大人的意思是,这背后确有权贵翻云覆雨?”
“我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他审慎作答,好言好语说尽,再苦口婆心劝慰,“年轻人,你的路还很长,莫要为了已故之人自毁前程!想想你的家人,难道你想你那尚未及冠的弟弟再遭一次牢狱之灾吗?亦或让你缠绵病榻的老母,为你忧虑一命呜呼!”
或是这一句饱含威胁意味的话彻底揭了徐稚柳的逆鳞,他当即翻脸。
“你卖官卖爵,唯利是图,审案不公,潦草塞责,多少无辜百姓枉死于你案下,你既对不起头上的乌纱帽,又何来资格对我评头论足?几个纸团就能引蛇出洞,显是你心虚鬼祟,如今还强自狡辩,意欲威胁,张文思,你罪该万死。”
“大胆!你满口胡言乱语,污蔑朝廷命官,信不信我立刻叫人将你拿下?”
“你深夜造访,不就是想避着人?若不怕亏心事败露人尽皆知的话,就随便叫人好了。”
“你……你你……究竟意欲何为?”
“我只想要真相。我想知道害我父亲的人究竟是谁!”
那一晚的后来,他被迫到无路可走,也想转嫁火力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不得已向徐稚柳吐露了“心迹”。
事实上,他也曾怀疑过文石因文定窑一案被人拿捏住把柄,不得已作伪证冤枉徐有容。如是推论的话,极有可能两宗案子存在一定联系,或许背后元凶是同一人。
徐有容一介书生,隐居瑶里,和文石八竿子打不着,生平也无相识的迹象,加之为人亲和,鲜少与人口角,更不会得罪谁以至非要他死不可。
唯一的可能是,他或许机缘巧合看到或接触到了消失的数十万两白银,以此遭人灭口。
可是,想要徐有容死,随便找个人就能杀害,何至于绕个大弯子,非要毁了他的清名不可?
以他断案多年的经验来看,这位“元凶”应是徐有容的熟人,且和文定窑有关。能吞下数十万两白银,若非权贵,便是深受权贵信任的马前卒。
除此以外,别无可能。
/
戌时一刻后,七真殿里恢复短暂的寂静。
躲藏黑暗数月以苟且偷生的张文思,回忆起当晚的情形,好像骤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思路清晰,有条不紊。他说那日和徐稚柳的对峙,说临走前再三提醒让他好自为之。可没有多久,他竟以身蹈火,殉窑而亡。
那样一个自诩清正的、恃才傲物的家伙,竟会自戕?他再一次被吓到魂飞魄散,伴随着夏瑛的死彻底没了生机。
他不得不躲到深山老林,流下似乎是懦弱又似乎是多年仕途不顺碌碌无为的泪水,为无力摆脱的困境而顾影自怜。
这些日子像个老鼠,成天在熏着檀香,画满灵芝八仙的道观里打坐,寻求让心灵平静和安定的道法,明知不可能而为之,他也快要疯了。
若当真是徐稚柳的鬼魂回来索命,干脆带他走吧!
他受够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折磨!
当真受够了。
他抱住随风而动的帷幔一点点滑落在地,整个人发丝凌乱,眼神空洞,望着不知哪一处,背脊落满灰。
徐稚柳临要出门前,似乎想起一事,驻足回首。殿宇内依旧黑暗空寂,四面窜风。他的声音又冷又涩,似从遥远的他乡破空而来。
或许是得偿所愿,这一刻的他忘记了伪装和矫饰。
“此前你因王进开始调查地下钱庄,可有收获?”
张文思摇头。
“镇上的钱庄都在徽帮人手里,为了对抗都昌帮,他们管理严格,轻易不让外人查探。何况,何况我怀疑是你所为后,就打消了对王进的怀疑。他……跟着我许多年了,一向忠直。”
徐稚柳嘴角微微扯动了下:“忠直之人为何不来救你?张文思,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的仁慈让我觉得可笑。”
出了山门,徐稚柳一路大步往前走,及至山脚下,零落星光闪在天边,两匹马孤零零打着哈欠。他猛一停步,看向身后之人。
自从入了殿,她再没说过一句话。
“你没有什么要说的?”
他这一发问似乎又带着莫名的气,而这一回梁佩秋没有客气却有力地回敬,只是静静看着他。
许久许久,久到徐稚柳心尖儿颤动起来,被她灼热的目光迫视到不得不偏过头去,藏起一丝狼狈。
这时她开口了。
“你带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一幕吧?你想告诉我什么,徐稚柳很可怜很可悲,沦为安十九的走狗只是形势所逼,身不由己,而我不仅利用了他,背叛了他,还误会了他!他背负血海深仇寄人篱下,好不容易有窥见天光的机会,我却逼得他走投无路,声名狼藉,以至投窑自尽……他的死是我造成的,是我害死了他,我应该感到愧悔自惭,甚至自裁以向他谢罪,对吗?”
“难道不是吗?”
“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不如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你知道这些?周大人,据我所知,你从未来过景德镇,这是你第一次调任出京,可你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远超寻常,你不仅知道百采新政,还知道陶业监察会是其最重要的一笔,你了解张文思和安十九,不仅了解他们的勾结和龃龉,还了解表面之下实际的虚伪,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你对徐稚柳……”
“住口!”
徐稚柳突然不想再听她说下去,她却不如他的愿,上前一步。带着那熟悉的、要命的苦橘香的气息,携着秋夜的寒意扑向他,他下意识后退一步。
不远处是万丈悬崖,在他一步接一步的后退中,她忽然停下,一把攥住他的衣袖。
“你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像……”
这最后的话,她说不出了。
他知道文石和徐父之死另有隐情,知道文定窑背后官权的串通,甚至知道她想借监察之名调查钦银贪污之事,而这些统统发生在他来赴任之前。若非没有人提前告知他这一切,他绝无可能短短时间调查清楚这些事。
而这个世上,能对此事知之甚清的,没有几人。
况且云水间是那人的私宅。
连她都是那人死后才知,旁人又怎会知晓他的秘事?
“告诉我,你究竟是谁?”
徐稚柳垂眸,视线落在她清瘦如柴的手腕上,尔后抬眸,看到一行清泪从她眼角滑落,喉头便似她一样,掉入哽咽的漩涡。
这几张有点像小情侣闹别扭,隔着面纱打拳头。
柳:汪汪汪。
秋: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