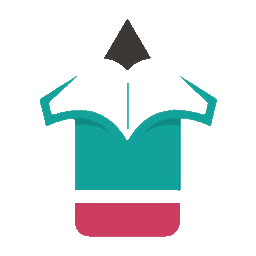阳光有些刺眼,海棠果分外红艳,应该是从暗处瞬间进入明处造成的错觉,也可能是头发入眼造成的不适。郑能谅有些惊慌,是刚才的突然袭击留下的余震,也有些愧疚,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秦允蓓的事,还有些担心,生怕被人撞见他和烂醉如泥的戴珐珧纠缠在一起的尴尬场面。
小麻花也对他的遭遇深表遗憾:“你说你,本来是她不省人事,你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弄成了你不省人事,她可以为所欲为。瞧你俩现在这姿势,莫非你喜欢被动?”
“你还喜欢被虐呢!”郑能谅正为戴珐珧三番五次的纠缠烦心不已,听小麻花的调侃便气不打一处来,猛地伸出脚尖一勾一提,顺手握住黄金分戈的柄,朝前横扫过去。
他本想虚晃一戈吓唬多嘴的小麻花,谁知它那根大舌头正好伸出来要反驳他,他收势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寒光四射的刃口迎上了唾沫四射的舌头。
“啊!”伴着小麻花一声惨叫,锋利的刃口瞬间没入舌头,阻力通过黄金分戈传到郑能谅指尖,吓得他慌忙撒手。戈柄一端重重砸在地上,将舌头往下扯出一大截。
“哎,哎……”小麻花又疼又急又气又口齿不清,“蛋勒,蛋勒……结尺额……”
郑能谅挠着头:“你在说啥?”
小麻花痛苦地翘了翘舌尖:“戈,戈,拔!”
“哦!”郑能谅重新拾起戈柄,定了定神,说,“你忍着点,我要拔|出|来咯。”
“嗯。”
“等一下!我这一拔会不会把整根舌头扯断?你会不会失血过多而死?我这算谋杀还是过失杀人?哦,你不是人……对了,突然拔|出|来的话,血不会溅我一身吧?这衣服可是小蓓送给我的新年礼物呢。咦,你这舌头上怎么没有血……”
“嗯嗯,嗯嗯,拔!开点……嗷!”
“呼,拔好了!嘿嘿,刚才我故意问这些废话,就是想转移你的注意力,这样拔|出|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疼了,电影上学的,聪明吧?”
“聪明个大头鬼,舌头差点让你扯断!给你脸了是不,敢对我下毒手!”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刚才就做个样子吓唬你,谁知道你真把舌头伸出来配合我了……”
“谁配合你了?你跟我斗嘴,我当然要回应了!”
“哎,一场误会,没事就好。”
“什么没事,这么大一窟窿!”
“坚强点,就当穿了个舌钉嘛,何况血都没掉一滴。对了,怎么没有血呢?”
“我是素问镜,又不是树袋熊,我们的生理结构又不一样,可没血不代表我不会疼啊!”
“啊,很疼吗?”
“你知道蛋疼有多疼吗?”
“呃,真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这么神通广大,黄金分戈伤不到你的呢。”
“你不是自夸很聪明吗,就不会想想,黄金分戈能割下树上的金蛋,我也是长在树上的,凭什么就伤不了我?”
“也对,可你们设计盗格空间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周到一些吗,比如把你的舌头设计成刀枪不入,或者在盗格者和素问镜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带,或者给你们素问镜罩个铁笼子,盗格者不就没有机会用黄金分戈伤害你们了?”
“铁笼子……动物园呢?养猴子呢?搞什么缓冲带?谁会想到有你这样胆大包天的盗格者!盗格空间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么过分的事!”
“有史以来?盗格空间也会修史吗?那我是不是会被加载史册?史上蹂躏素问镜第一人,哈哈哈!”
“史上最不守规矩、最喜欢抬杠的盗格者还差不多。懒得跟你废话!你该做选择了,后会有期。”
“哎,这就溜了?我还有个问题没问呢。”
小麻花把舌头往前一伸:“戳了这么大一窟窿,还好意思问问题?!再说,刚才聊了半天,你也没少问吧!”
郑能谅面带愧色地看了眼它舌尖侧面那个拳头大小的洞,舔了舔嘴唇,诡辩道:“刚才聊的都是私事,这个洞也是私人恩怨,我现在要问的是关于人家姑娘未来命运的问题,咱不能公报私仇不是?”
“舌头不方便,下次再跟你斗嘴,拜拜!”话音未落,那根麻花舌就哧溜一下缩进树干里去了。
郑能谅只好独自面对选择,定睛一看离他较近的那颗金蛋,脸瞬间红得像满树的海棠果。画面上,戴珐珧背对着他,身穿白色浴袍站在衣柜前,左手一件蓝色吊带背心,右手一件红色连衣裙,对着镜子来回比画了几下,摇摇头,统统丢到一边,又取出一件宽大的黑白格子衬衫,一试,笑了。她抬手在胸前轻轻一拨,浴袍像瀑布般落下,露出令人窒息的胴体。
面对这火辣的一幕,郑能谅更多的感觉是紧张和羞愧。在浴袍滑落的同时,他下意识地捂住了眼睛,这并非在装清纯,装也没人看。他只是觉得偷看朋友的身体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何况她还对他表达过好感,而他又拒绝了她,但他马上又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看,因为他必须对画面进行判断并做出选择。他深吸一口气,悄悄张开指缝,发现画面上的她并没有转过身来,也没有穿上衣物,就那么亭亭玉立在镜子前欣赏着自己的身体。他试着缓缓放下手,用一种调查研究的眼光去直视画面,把镜前的她当作一件事而不是一个人来看。起初他发现很难自欺欺人,但一想到秦允蓓,想到她的美,想到她的好,想到她还在外面的某个包厢里等他回去,他就豁然开朗了。他终于明白,眼前这位姑娘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是命运安排的一场测试。他也渐渐意识到,在盗格空间,他面对的不只是未知的困惑,还有无尽的诱惑;选择的不只是别人的未来,也是自己的人生。
郑能谅认真地观察这个画面,不再有杂念,只见戴珐珧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身体,忽然转过脸来,冲他嫣然一笑,仿佛知道他在后边窥视一般。这个诡异的举动让他爆出一层鸡皮疙瘩,刚要开口对画面里的她做解释,就发现这个想法实在荒唐可笑——金蛋只是预示未来,可从没听过能跟未来的人交流,若是能交流的话,那选择似乎也容易多了。
他定下神来,又仔细看了看画面,终于发现刚才不曾注意到的细节:透过镜子的反射,可以看到在她身后的双人床上,铺着一床厚厚的被子,被子与床头灯相交的位置,歪着一颗脑袋。戴珐珧刚才的回眸一笑,是给床上那人的。
郑能谅长舒一口气,可这口气刚呼出一半便戛然而止:床上那人竟然是他!
他的大脑一片混乱,不知这是小麻花跟他开的玩笑,还是他眼花看错了。他使劲揉了揉眼睛,又确认一番,这不是玩笑,也没有看错,那眉眼、那酒窝,除非他还有个双胞胎兄弟。“我怎么会在她床上?下个猴年马月……五年后?我们都毕业了,小蓓呢?阿珧的男朋友呢?我跟她这样亲密……不会触发盗格空间吗?到底发生了什么……”海棠树的叶子和果实没有兴趣听他的自言自语,匆匆而逝。
郑能谅也不敢再多想,手起戈落,让这颗金蛋和那香艳而古怪的未来画面一并归于尘土——无论这一幕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他都不想让它在未来成真,不愿让秦允蓓因此受伤害。
完成了选择的郑能谅如释重负,忽然想起树上还有另一颗金蛋没看,虽然现在已无法再选择,但他还是好奇那是一幕怎样的未来。他仰起头,刚要向枝叶深处望去,就觉得眼前一黑,瞬间被送回了现实世界。
“不可能,他从不喝酒的,他酒精过敏呢。”耳畔传来秦允蓓的声音。
“那就不知道了,我们包厢的衞生间被人占了,我只好出来找地方方便,一进这屋,就看见他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以为是喝醉了,也没多问。”伴着抽水马桶的冲水声和翻盖声,戴珐珧从衞生间走出来,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朝沙发看过来,发现郑能谅睁开了眼,便笑道:“喏,他醒了,什么情况你问他吧。”
秦允蓓低头一看,又喜又急:“你没事吧,怎么睡得跟死猪似的?幸好遇到阿珧,不然被人拐卖了都不知道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郑能谅和她一样困惑,冲戴珐珧问道:“你不是醉了吗?怎么……”
“是啊,刚吃了点醒酒药,头还疼着呢。”戴珐珧一边把纸巾丢进垃圾桶,一边揉着太阳穴。
“你怎么知道她醉了?你不是晕在沙发上吗?”秦允蓓好奇道。
郑能谅瞥见戴珐珧偷偷对他使了个眼色,意识到刚才那一幕谁也没法解释清楚,为了不让秦允蓓起误会,他只好顺着戴珐珧的话编下去:“是这样的,小蓓,你刚才醉了,我就出去给你买醒酒药,回来的时候进错了包厢,一推门就撞见个发酒疯的醉汉,硬说我是他未婚妻,要跟我去拜堂,拉拉扯扯起来。那家伙块头大,我哪是对手,被他一掌拍在额头上,本来就有伤,就晕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迷糊间看到有个人影摇摇晃晃闯进了衞生间,不用说又是个醉鬼。我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的晕劲还没过去呢,就继续躺着休息了,没想到这人是阿珧。”
戴珐珧心裏清楚,郑能谅在借瞎编的醉汉调侃她刚才的失态之举,便冲秦允蓓笑笑:“对了,上次在俱乐部,你帮了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唉,我今天真的喝太多了,不过你千万别误会,我这人喝多了只瞎说,不瞎搞,我跟他孤男寡女在这屋里可什么都没做哦。”
郑能谅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马上接过话茬开玩笑道:“孤男寡女要做点什么,都会先把门反锁上的,哪能被人这么容易捉个现行嘛。”
“那是,像你这样裹得严严实实跟个因纽特人似的也做不了什么。倒是我,一看就是个不三不四的交际花。”戴珐珧嘴角挂着自嘲的笑容,幽怨地打量着自己,话里的酸味越来越浓,似乎刚才的醉意还未散尽。
心直口快的秦允蓓全然没抓住这番话的重点,还一个劲地哄她:“哪有,你这套衣服可衬你的身材了,我就是肚子上有些赘肉,没有自信穿成你这样,羡慕都来不及呢。至于他呀,一直都那么古板保守,夏天也穿长袖长裤,别提多丑了,好像露出点肉就会被人占了什么便宜似的。你忘了,上次去游泳,他还穿了套潜水服呢,蛤蟆皮,哈哈!”
郑能谅不想再讨论衣服、身材、孤男寡女之类的话题以免节外生枝,便对秦允蓓说:“好了,时间不早了,阿珧喝了不少酒,你刚才也醉得不轻,改天再聊吧。”
“你不说我都忘了呢,我的几个狐朋狗友还在那边包厢里嗨歌,”戴珐珧自知在正主面前不宜过多纠缠,便对两人挥挥手,“那就不送二位了,祝你们一路顺风、一夜好梦。”
秦允蓓心底一暖,一边扶起郑能谅,一边翻他口袋:“你刚说给我去买的醒酒药呢?给阿珧用吧,她更需要。”
郑能谅刚才只是借口买药出来找祝班长,身上哪有什么醒酒药,正尴尬间,却被戴珐珧及时解了围:“不用找了,刚才我进屋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一盒,以为别人掉的,就顺手拿来用了,不然也不可能这么活蹦乱跳地跟你们聊天了。”说着她在身上飞快地摸了一通,又转身看看衞生间,嘟哝道:“剩下的那些,我记得好像放在柜子……还是马桶盖上的,啊,不会被我稀里糊涂冲走了吧?”
秦允蓓连连摆手:“不用找了,酒醒了就好。”
郑能谅暗暗佩服,戴珐珧这一番话和表演既填补了他刚才那个故事里道具的漏洞,又解释了她短时间内从醉酒到清醒的转变,还完美地勾勒出一幅孤男寡女在包厢里和谐共处的画面:他在沙发上昏睡,不具备作案能力;她在衞生间里吃醒酒药,不具备作案时间。
告别了戴珐珧,两人离开包厢,穿过迷宫般的长廊,朝大门走去。秦允蓓紧紧握着郑能谅的手,尽管隔着手套,他的掌心仍能感到源源不断的温热。
外面下着小雪,站在路边,秦允蓓玩性大发,张开双臂在风中转了好几个圈,笑声和舞步震动了苍穹,抖落漫天雪花。因为刚才的遭遇和谎言,郑能谅还陷在不安中,双颊滚烫似火,令白色的精灵们一触即融。他用力搓了搓脸,说:“没发现啊,你酒量这么好。”
“你没发现的事还多着呢。”秦允蓓做了个鬼脸,拽起他冲上了刚刚靠站的公交车。
投完币,落了座,他轻声追问:“还有啥我没发现?”
“嘘……”秦允蓓竖起食指,“听,好空灵啊!”
驾驶座旁斜插着一部调频收音机,正在播放西都音乐台的《交通之声》,郑能谅一听便知这一曲是恩雅的《放逐》,几个月前在杰叔的网吧里就被网管的循环播放洗了脑,一口气买了好几张她的专辑。
他笑着点点头,轻轻揽过秦允蓓的肩,一同欣赏这首能让人瞬间安静的神曲,无论驱除雪夜的寒冷,还是化解尴尬的气氛,它都能不辱使命。
回到宿舍后,郑能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今天去找祝班长的决定似乎有些唐突,也许他提供的凶器线索有助于找到真凶,却也可能对祝班长的情绪和计划造成意外的干扰,使其做出不安全的举动。这就如同在盗格空间选择未来,有时一个出于善意的、看似有益的选择,却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他想起了八年前第一次在盗格空间做出的那个选择,不禁更为祝班长担心。
几天后,郑能谅一个人跑去陌上珠夜总会找祝班长,却听领班说他已经辞职了,而且没人知道他的住址和联系方式。郑能谅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连忙到市公安局报了警。做笔录的是位面善的年轻警官,姓吕,问得很仔细。为了让事情听上去合理可信一些,郑能谅没有提暴露凶器的那场袭击,也没有提一波三折的包厢密谈,只说祝班长是在独自追查女友玉儿被杀真相的过程中突然失去联系的,并告诉吕警官,曾听祝班长说过有个绰号叫“蛇皮”的刺青汉子与玉儿的死有关。核对完笔录并签字后,郑能谅留下了吕警官的联系电话便回去了,接下来所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