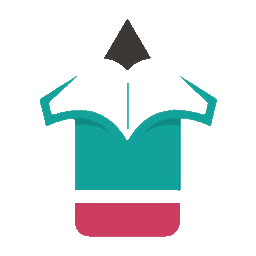第352章 弹压,暴动
夷安县。
大批百姓聚集在官府门口。
他们没有表现出过于激烈的动作,但眼中流露出了淡淡的不满与失望。
一个人在生活中遭受苦难,可以归咎于时运不济,没有足够的努力,但成百上千人都在遭受苦难,那就不再是时运,而是整个时代的问题。
七国之叛,主谋荆国,齐地诸国则属于从犯。
后世烧死钦差大臣,导致本该起飞的区域沦为平庸。
按罪行来估量,起兵叛乱明显更加严重。
故而终景帝一朝,齐地无论是诸侯国还是郡县,其实都不怎么受到待见。
荆国拆分为郡县之后,在文书上基本避免使用“荆”这类字眼,可齐地郡县和诸侯国,却无法避免使用“齐”“胶东”“胶西”等文字,相关的称谓已经约定俗成了近千年,一时间根本改不过来。
刘启明面上不会有任何表示。
因为内心的喜好擅自更改大量地名,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统治者该做的事情。
但他刚坐上王位两年,这片地区就起兵造反,差点因此被掀下皇位。
朕还得对这些地方产生好感不成?
齐地长期没有政策扶持,也就显得没有那么奇怪了。
不过齐地作为楚地和燕赵乃至三河地区的中转站,靠着过路的商队,同样可以吃得盆满钵满。
过路的关税可以供给官府,稍微漏下来的一丁点油水便可以肥了无数百姓。
因此齐地大部分地方的百姓都能够自力更生,何况临海地区可以煮盐贩卖,更是一项不错的敛财手段。
但这与胶西国统统无关。
刘端在上位之初尚且收敛,但在宫廷变故后,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神经病。
上行下效。
胶西国便在他的治理下,官吏明目张胆地搜刮商队的过路费,在贪污腐败的路上越走越远。
各个地方的商贾亦不是傻子,在胶西国吃过亏的,自然没有道理去栽第二下跟头,听闻过胶西国恶名的,当是敬而远之,不去自讨苦吃。
大量商队绕行胶西国,想凭借商业恢复战后的创伤,成了妄想。
可靠着农业发展,百姓又不得不面对胶西国官吏的横征暴敛。
大汉太平,其他郡县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胶西国却如同一潭死水,没有任何动静。
因此墨家弟子在集市、田垄上稍作鼓动,就有一大批农夫与小贩选择跟从,来到了县衙外游行示威。
守门的差役见状,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府内,将大门紧闭。
面对三五个“暴民”,他们尚敢靠着身上这层皮去狐假虎威,但面对数百名愤怒的百姓,他们只能躲回县衙内瑟瑟发抖,然后向上禀报。
“你去跟明府汇报,那些乱民又来了。”关上大门后,稍稍松了口气的胖差役对同伴道。
“唉,这都是什么事啊。”另一名瘦差役叹了口气,“短短旬日,这些人来了三回,最短也得待五六个时辰,阿母和内人深怕我出事。”
“可不是。”胖差役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你说我们又没招惹他们,没事来堵门,这让明府面子上不好看,也是让我们为难,真不知道这些人图啥。”
“行了行了,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和明府汇报。”瘦差役摆了摆手。
两人对此事的立场和观点有些偏差,聊不到一块去。
瘦差役前去找县令,发现县尉亦在屋内,汇报完毕后,便退了出去。
待他离开之后,室内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庞县尉,你之前不愿意用武力的手段解决这件事情,我能够理解,但现在王上的命令已经传达下来了,伱还坚持原来的观点吗?”白县令语气平淡,但所说的那些话却不客气。
庞县尉揉揉眉心,“外面少说得有两三百人,我带着二十来号弟兄出去,宛如石头砸入水中,溅起一簇水花后,就会没了消息。”
“庞县尉,我相信你的能力。”白县令呵呵笑道,“你这块石头砸出去,是砸到冰面上,能把那些暴民砸个头破血流,砸个粉身碎骨!”
他和县尉算是平级,没有将对方直接扳倒的确定,强行下令只会将关系闹掰,以后共事起来,尴尬不说,工作更是难以开展。
何况对方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屈重吟的徒孙。
咬了咬牙,庞县尉梗着脖子道:“可以或许可以,但我不愿!”
屋内一阵沉默。
“庞县尉,我初来夷安县的时候,还在疑惑,像您这样有能力又有关系的人,为何会屈身于小小的夷安县十余载,始终未能得到升迁,今日我算是明白了。”白县令站起身来,“王上的命令是驱散暴民,并找出典型狠狠惩戒,这事你不干,那我干。”
说罢,他走出门去,独留庞县尉在屋内。
“唉。”
端坐良久,听着外面召集差役的声音,庞县尉长叹一口气。
自己师爷在代地办案,如鱼得水的情况,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前有阳夏文贞侯担任国相,抗下所有压力,后深得代桓王信任,奉旨办案。
自己空有能力和抱负,却在小小的夷安县内郁郁不得志。
或许这就是命吧。
……
白县令召齐差役,让他们带上棍棒,眼神冷冽地打开了大门。
“官府重地,聚众闹事,可知罪否?”他一出门,便先声夺人,将事件定性。
这件事情是王上交代下来,需要大办特办的案件,那自己定然需要扩大化,至少得有三四十个人头才算交差。
“县尊,今岁的刍藁是不是收得有些早了,地里的麦穗都没长出来,哪有刍交啊。”
“那些差役日日来集市拿取物件,分文不给,县尊能否管管。”
“我听说国相想要做事却患病了,您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吗?”
“县尊……”
白县令的额头暴起青筋。
这些暴民,是没有听见自己的话吗?
如果他们开始逃窜或者跪地求饶的话,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但现在就别怪自己心狠了。
白县令朝着身后挥了挥手,“上去打,把这些乱民给打走。”
“诺。”一众差役从府中涌出,威风凛凛地挥舞着棍棒,砸在前排普通百姓的身上,一时间吓得不少人脸上变了颜色。
若这真是一场普通的聚众抗议,说不定这波强行镇压,真能起到效果。
但这两三百人当中,混杂了大概三成墨家弟子。
他们过来,可不是为了身处前排看热闹,而是为了处理突发情况。
但是这些墨家弟子还真没有想到,县令居然真敢选用武力手段驱逐百姓。
按照他们原本的计划,官府持续不回应,当缩头乌龟,完全没有关系,他们自有渠道将这边发生的事情传到长安去。
可对方选择动手,岂不是送了更好的由头?
年轻的墨家弟子的眼中冒出兴奋的神色。
“我们只是来要个说法的,但说法没有要到,反倒要挨打,要被抓走,这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天理了?”
“我是来要解释的,你们想干什么?”
“现在跑了,等下他们就会去我们家里抓人,不如和这狗官拼了!”
“我们人多一起上,法不责众。”
墨家弟子吼叫着,拿出准备好的锄头和鱼叉就上了。
来抗个议,带着吃饭的家伙,没有什么毛病吧?
有了主心骨,边上的那些刚打算逃的窜普通百姓,顿时止住脚步,纷纷回首。
墨家弟子中有两句话最触动他们。
其一是现在跑了,也会被官府的人找上门去。
拥有理智者稍作思考,便可以明白这话的含义。
他们本就是用游行来向官府施压,借此减轻差役催促刍藁征收的压力。
可白县令的态度,完全看不出任何谈判的意愿。
要是事后追责,分散开的两百来人在那些恶狠狠的差役看来,与砧板上的鱼肉,狼群中的羔羊,没有任何区别。
外加这次前来抗议的队伍中,总归有自己认识的人,到时候对方被抓住了,难道指望他不要把自己攀咬出来吗?
于是此言杜绝的,乃是这些百姓的侥幸心理。
与其畏畏缩缩去赌运气,不如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其二是法不责众。
要是二三十人和官府作对,那让他们加入进去,断然不敢。
但如果是两三百人和官府发生了矛盾,关联的人家差不多有整个夷安县的一成半。
如此一来,百姓心中便有了底气。
自己并非无端犯事,总不能说将我们这些人全部砍脑袋吧?
那夷安县的稳定还要不要了?
来参加游行抗议的百姓,心头本来就怀有怨气,以及夷安县民风剽悍,要不墨家弟子亦不会一呼百应,轻松喊来好几百人助阵。
何况在群体情绪的感染下,大部分人会做出平日里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就比方后世去观看一场大型球赛,哪怕不是球迷,亦会被身边那些人的情绪感染,在进球的时候起身狂欢,或者在失误时愤慨地破口大骂。
现在有了几十个人的带头,加上给出了冲分的理由,于是县衙门口游行的百姓们反身朝着那些差役扑了过去。
瞬间,攻守易形。
夷安县的那些差役,完全没有想过外面这些百姓会敢反抗,因此手中拿着的大多是木棍,未有持开刃兵器者,至于甲胄之类重器,更不可能出现在县衙差役的身上。
在兵甲上没有代差存在,差役在人数上的十倍劣势,就显得极为明显。
身在前排,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几名差役,握着棍棒末端,竖劈横扫,欲将那些百姓再度驱散。
他们的攻击砸伤了三五人手臂,又暂时逼退了周围的一小圈人,但待到拿着鱼叉的渔民,或扛着锄头的农夫跑过来,将他们手中的木棒架住,那周围的百姓再一拥而上,将这些走狗淹没在人海之中。
前排的差役坚持不到十五息,全盘溃散。
后面的那些差役,看到同伴的惨状,顿时心头一紧,害怕和恐慌的情绪油然冒出。
我一个月就那么几贯铜钱的俸禄,完全没有拼命的必要啊,而且这些暴民看上去实在过于凶恶,不是自己可以对付的了。
退意萌生起,刹那天地宽。
随着第一个差役抛下手中的木棍,拔腿开溜,剩下那些差役当然不会杵在原地,他们有样学样,只恨自己没长八条腿。
看着如狼似虎般冲来的群众,傻眼的反倒是开始作威作福的白县令了。
嗯?
嗯嗯?
现在的事态发展怎么和我想得不太一样啊!
当他意识到自己同样该跑路的时候,身前已经没有了差役,落到了最后。
气急攻心,白县令心中唯剩恼怒,这帮家伙,不知道提醒一下他们的县尊吗?
冲着他们这个表现,自己之后必须要狠狠责罚。
他的心神稍有分散,没有注意脚下,踩到一根差役丢弃的木棒后,滑倒在地。
外加白县令身上所着乃是官服,本就不适于跑步运动,后面追赶的百姓则是短衫与褐衣。
于是他刚刚爬起,没有跑出几步,就被众人团团围住。
“你们想干什么?还不让开,想都被抓进牢狱是不是?”白县令色厉内茬地威胁道。
众人沉默一瞬,接着爆发出轰然的唾骂声。
“恬不知耻!”
“打死这个狗官!”
————
众庶聚于县衙,言不平事,触怒端,令官吏驱,伤者数十。
民怒,入杀县令。
传至长安。
赵绾上言:“臣闻仁君不畏逆耳之言,胶西有变,自有其故,应广纳民意,得知事实,以示圣朝无讳之美。”
帝意乃悟,诏谴郡县,见民广言。——《资治通鉴·汉纪九》
————
汉武帝建元年间,夷安县发生了一起百姓暴动。
夷安县属于胶西国治下的县城,人口大概在三千户,因为七国之叛的缘故,民生建设尚未恢复到大汉平均水平,偏偏又摊上了胡作非为的领导班子。
于是在重重积压之下,民众开始冲击县衙,甚至杀死了夷安县的县令。
如同煽动风暴的蝴蝶翅膀,夷安县的暴动案件震动长安,成为了引爆胶西王案的导火索。——《显微镜下的大汉》陈泺